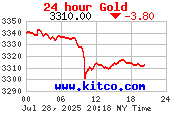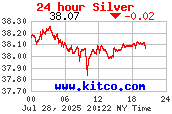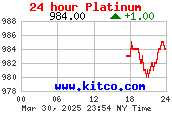郎咸平
溫州動車追尾是如此的讓人痛心。近期高鐵意外頻發,是天災,還是人禍?我們到底有沒有必要搞高鐵?之前我們說過了經濟爲何恐慌,通脹我們慌,房價我們慌,現在,鐵道部引以爲豪的高鐵給我們製造了更大的恐慌。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鐵道部是這麽說的,這位“鐵老大”認爲,包括以前的新聞發言人,包括現在的鐵道部的領導,在接受記者提問的時候都會說,要解決春運難問題,我們就要加大運力,提高運速,而如果我們想把這個運輸能力提上去的話,我們就必須搞高鐵,也就是要更快地到。比如過去是50個小時到,現在5個小時到,這樣不就解決問題了嗎?但問題在於,我們鐵道部的同志完全搞錯了。增加運力是什麽意思?是要增加火車發車的密度。比如說上海到南京的路線,原來是兩種動車,一個是250公里每小時,一個是160公里每小時。注意,這兩個數位非常重要,各位想想看,如果一條鐵路,它的火車都是跑250公里每小時的話呢,它就可以一趟接一趟地跑,不需要等候。可是如果這個鐵路一會兒是300公里的,一會兒是100公里的,如果再加上更慢的貨車的話,那是不是就要排隊等了?那這個密度肯定就稀鬆了。
就拿日本、德國的鐵路來說吧,它們的速度不是最快的,德國高鐵的水平大部分是我們動車的水平,基本達不到350公里每小時的,大概也就一兩百公里吧。但是,它們運輸的密度是我們高鐵的30倍,而且非常穩定。因此現在的問題是什麽?如果說德國高鐵的密度是我們的30倍,那就說明我們還有往上走的空間。也就是說,我們真正的問題是管理的問題、軟體的問題,而不是硬體的問題。而且我們目前絕對有能力讓人人都能買到票,完全解決運輸的問題。這些鐵道部門的同志們完全不曉得什麽叫做鐵路經濟學。鐵路經濟學要的是在保持一定速度的前提下,不是追求更快,而是講究密。而在達到密之前,每一列火車跑的速度必須是一樣的,這樣才能一列接一列地跑,才能密,才能達到30倍的運力。當然,其實對於我們來講,不要說30倍,只要增加3倍我們就能解決很多問題。
還有這個所謂的能達到350公里每小時的高鐵,各位不要被這個宣傳誤導了,各位曉不曉得,整個從南京到上海,能跑到350公里時速的路段只有12公里,其他路段不是曲度太大,就是地質不穩,速度根本快不起來的,只能在100到250公里之間運行,所以它的速度和動車是一樣的。從上海到無錫,一列高鐵叫G7003,全程要1小時7分鐘,但是D307只要58分鐘,你看到沒有,動車還比較快些,這樣的話,你這個高鐵還有什麽意思呢?這不是資源的浪費嗎?這種大量的浪費,誰來負責?而且,這也完全違背了我上面闡述的鐵路經濟學,因爲你沒有密度嘛。
所以說,我們的鐵路部門根本就沒有搞清楚我們提速的目的。我們提速的最終目的是什麽?是爲了提高運輸效率。效率沒有提高,你光是解決速度有什麽用呢?對於我們鐵路部門來說什麽是效率,效率實際上就是把千百萬人在春運的時候運回家。我們應該關切的是,讓這列火車盡可能多地把人運回家,而不是讓一部分人盡可能快地回家。更搞笑的是,在這種運力緊張的時候,我們又充分發揮了我們的創造力,搞了個超級豪華軟臥,我們老百姓需要這個東西嗎?還有一些人吹噓說,這是我們的自主知識産權,是有市場的。我發現啊,我們自我感覺實在不是一般的良好。
請各位想一想,現在我們國家不是把大量資源投放在解決鐵路運力的密度上,就是我剛才講的,不是增加綠皮火車的運力,而是把大量資源投到一些毫不實際的高鐵和動車上。
現在更可怕的是什麽?我們産生了高鐵崇拜,叫做高鐵“大躍進”,這個高鐵“大躍進”本身,真是太可怕了。我舉個例子,在我們“十二五”規劃當中,在2020年之前要興建的高鐵是畫實線的,2020年之後呢,考慮要建高鐵的,或重新規劃的畫虛線,但是我們現在發現,很多的虛線現在都變成了實線,比如說鄭渝高鐵、昌吉贛高鐵,還有贛州到深圳的高鐵等等,它們應該都是畫虛線的,結果現在的計劃是要在2013年通車!還有,新疆也規劃了3000公里高鐵,它竟然也需要高鐵!我對此感到不可思議。還有從昆明到拉薩的高鐵,昆明段也在興建,各位,我們真正需要的是什麽?是老百姓致富,是要讓老百姓更富裕,這才是我們應該做的事,而不是用那麽多錢和精力搞個高鐵。
如果是爲了老百姓致富的話,搞些綠皮車的建設完全夠用了,搞高鐵的話,可不是爲了老百姓更富裕,而是爲了旅遊的人,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
我的建議是什麽呢?取消動車,取消高鐵。當然不是完全取消了,只是不要再大舉興建這些東西了,這些都是好看的好玩的,我們統統不要,我們希望鐵道部門能夠讓綠皮火車增加密度,固定時速的密度,能夠像日本、德國一樣,增加幾十倍的運力,這不但不需要多加錢,相反還可以降低成本,然後票價還可以下降,讓老百姓真的能夠又快又便宜地回家過年。
現在每年需要我們鐵路輸送的是2.3億人,對不對?大概總收入是240億,那你拿出120億來,讓老百姓票價減一半可不可以?學生票價可以減一半,農民工爲什麽不可以呢?你這個暴利爲什麽不能拿來回饋給我們老百姓呢?我們今天的要求是什麽?是要求鐵路拿出一半的收入,讓老百姓票價減半,同時我們還要求,不要搞高鐵“大躍進”,要回歸過去的淳樸,要藏富於民。如何藏富呢?增加綠皮火車的密度。這是我們的建議。要知道,高鐵規劃就是兩三萬億,而每年春運2.3億人次,其收入才240億,這就意味著投在高鐵的這三萬億的資金,能讓我們的春運免費100年。如果這樣的話,我們還有必要搞高鐵嗎?現在有句口號,叫“高鐵開啓幸福時代”,那我的呼籲就是“綠皮車讓民衆回歸幸福時代”。
各位知道讓我們鐵道部官員感到驕傲的是什麽嗎?是我們高鐵的長度全世界排第一,我們高鐵的速度全世界排第一。但是各位曉不曉得,我們這個高鐵的成本爲什麽這麽高?如果你問相關人士的話,他們基本都會說,不是我們收費高,而是成本高。爲什麽成本高?因爲有技術轉讓費。
他們自己吹牛說我們掌握高鐵的關鍵技術。各位知道這些人是如何定義掌握關鍵技術的嗎?非常可笑的,他們認爲,超過15%以上的技術是我們的,就算我們掌握了關鍵技術,雖然85%是向別人買來的,只要自己占15%,就算我們的自主知識産權。那各位曉不曉得,我們爲此要交多少錢?我告訴你,每一列高鐵列車,我們大概要交2.5億元人民幣,在這之外還有8000萬歐元的技術轉讓費。這是什麽?這是典型的“我們得面子,外資得實惠”。
像這種鐵路“大躍進”的瘋狂之後,鐵道部不小心吐露了我們的負債比例,是56%。怎麽得出來的?我們做了一個計算,全國鐵路的年收入大概3778億元人民幣,盈虧剛好平衡,不賺錢。但是如果建高鐵的話,至少需要2萬億,那麽一年利息支出大概就是500億,我請問,你還這個利息的錢從哪里來?即使我們把慢車和快車都停掉,全部“被”高鐵,“被”動車,大概收入也只能增加5%,也就是200億,這200億還不夠交500億的利息支出,這還不算本金。那你這筆賬是怎麽算的?最後由誰來買單?說到底還不是慢慢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這樣做的結果是什麽?就是大量資源轉到政府手中,轉到外資手中,我們老百姓呢,就更貧窮,消費能力更低,內需更拉不動。在經濟學裏面有一個詞叫適當的發展模式,就是Properly。什麽意思呢?就是說我們的基礎建設千萬不能超前,爲什麽?因爲它佔用了大量寶貴的社會資源,其實我們完全可以拿這個資源用來創新、創業,讓企業創造利潤,讓老百姓更富裕,做到藏富於民。等到我們老百姓真正需要用到高速公路的時候,需要用到高鐵的時候再建。因爲這個東西非常貴,一下就幾萬億,如果我們把整個社會資源都用到超前的高鐵,超前的高速公路上的話,我們如何藏富於民?要知道,一旦花了就沒有了,大量的資源流失之後,企業利潤下降,老百姓消費下降,經濟隨之下滑。這叫什麽?越建設,越發展,老百姓越貧窮。這是一種“失當”,而不是“適當”。
-----------------------------------------------------------------------
思想花園
不可思議的高鐵應急燈
一場百年不遇(不是物理意義上的)的大雷電,驚醒了中國的高鐵夢。
整個事件過程中,讓我覺得最不可思議的是,事故發生後,車廂裏竟然是漆黑一片,沒有應急照明燈!
記得上兩個禮拜和幾個博友飯聚,有人還問我中國的高鐵有什麼新看法。我當時的看法是三點:第一,中國高鐵短期內必然將出一次大事故,事故過後,中國高鐵將再受一次打擊;第二,中國主動放棄在巴西的高鐵計畫,說明高層也知道自己的技術不過關;第三,劉志軍真是禍國殃民,私自把客運專線變成高鐵,尾大不掉。
溫州鐵路事故,由於是發生在中國技術標準最高的鐵路(該段是I級,是最高級別),暴露出背後的很多系統性問題。如果說,2008年膠濟鐵路死亡70人,是因為那條鐵路是臨時線,還可以理解,那這次溫州鐵路事故真是不可原諒了。
雷電令列車停下,停下的列車無法發出信號,提示後面的列車,這些都是很低級的技術問題,竟然發生在技術最先進的動車上,只能說明,問題是系統性的,而不是個別事件。
京滬、和其他高鐵的安全,真是令人擔心!
為什麼列車發生事故後,後備照明系統沒有啟動?難道沒有裝應急燈?為什麼玻璃砸不開,讓人無法逃生?
這些事情雖小,但正反映了,高鐵的設計者,在安全問題上,是如何的漫不經心!
溫州事故的死難者,主要是因為高架橋的緣故,從高處墜落,這說明高架橋的設計,是何等的危險。京滬高鐵一半路段是高架橋,還要趕工,趕及黨慶獻禮,何等兒戲。
以前曾經提過,鐵道部從來對廣深港線不感興趣,那時還以為是因為一些發展戰略的原因,現在想來,非常簡單,高鐵香港段很難撈錢,鐵道部自然不感興趣了!連鐵道部長都可以在招標上撈8億,那麼,那些機電系統,信號系統,其中上上下下的腐敗可想而之。
鐵道部第一時間把出事的車廂就地掩埋了,把上海鐵路局長撤了(估計過一段時間又會在異地任職,新的上海鐵路局長早前就是因為膠濟鐵路被處分的,現在又上來了),這些都很難挽回聲譽。
應該做的是全面的審查,甚至所有高鐵停開,人命關天,不應該是這樣糊弄過關的。
2011年7月25日星期一
高鐵時代的恐慌、不可思議的高鐵應急燈
2011年7月24日星期日
特首民望拾級而下 本是黨的理性期望
練乙錚
王光亞談挑特首條件干涉特區內政,港人口誅筆伐一點沒錯;但筆者認為,王所提三點,乃給梁、唐、范三位覬覦特首大位的候點人各戴一頂高帽誇獎一下而已,並無令某方特別得益。
王說的條件一,是「愛國愛港」。港人知道,這個有點拗口的外來四字熟語意即「愛黨」,此高帽切合三人頭形,但顯然是特別送給梁振英的,因為由他戴最富隱義。條件二,「要有很高的管治能力」。三人當中,唐英年管治經驗最豐,故這頂高帽給他戴,雖然尺碼大了點。條件三,「在香港社會有比較高的認受度」,這頂高帽,現階段送給民調領先的范徐麗泰最恰當。各人一頂,無分軒輊。
從江澤民「死訊」談起
然而,王氏說的條件三,包含一層深義,關乎今天共產黨在挑特首事上如何看待、特別是如何利用本地民意,坊間一般錯讀漏讀,值得在此詳細分析。論述此點,最好從周前傳出的「江澤民死訊」談起。
港人對這位常在鏡頭面前出洋相、因而有點人性味道、乃至娛樂價值的前任黨領導,不一定無半點好感。不過,河水不混井水,井中蛙王,對河魚而言,終是異物,談不上有真感情。然而,江、胡有隙乃不爭之實,故江何時死、死了沒有,能影響下一屆特首人選,港人因此關心。一般認為,三位候點人各自背後的人脈幫派關係十分重要,唐氏既親江,江不死則唐上位。這種看法失諸粗淺。
筆者現提一個不同觀點:江、胡對特首的功用有不同理解,挑怎樣的人或哪一個上位,由是有所爭持;至於各候點人與江、胡兩派的關係深淺,倒非關鍵,反正誰當特首也須完全聽命中央,言談舉止,遠近皆在黨的視線之中,巨細無遺。
幾乎已可蓋棺論定,胡乃過渡人物,作用僅在於把政權從第一代革命領導群(毛、鄧、江等)手上,穩當傳到第二代太子黨手上。胡本身並無堪足稱道的實踐建樹,迄今重大成就只有兩個,即搞好京奧、築牢綠壩;前者是形象工程,後者乃實質維穩,一個表,一個裡。
理論方面,所提出的「建構和諧社會」口號,與近十年來日益惡化的社會矛盾完全脫節,不啻天方夜譚。其剛毅木訥形象,到頭來不過反映必須謹小慎微,似台灣當年替老蔣傳位小蔣的過渡總統嚴家淦。
江搞革命出身,手筆比胡大,他可以一聲號令破天荒讓資本家入黨;他有膽在所有高幹及家屬(包括自己家屬)與中外資本家拉幫結派成為既得利益之時,指中國社會「有可能」出現一個既得利益階層;他能駕馭黨內不同派系,若非所願,起碼不會讓諸如薄熙來等的一方勢力,把未經批准的政治運動如「唱紅歌」一直由地方搞到京畿。
兩代黨領導的格局大小,亦可從江、胡各自委任了什麼樣的香港特首看出。董建華無管治經驗而主有為,江敢委任他,而且給他相當大的活動空間;曾蔭權有管治經驗而不敢為,胡才委任他,並只准他接「柯打」,利用自己的高民望,替共產黨在香港辦一些他力所能及、卻是共產黨不能輕易辦到的「好事」(如堵五區公投之「漏」),以後少給北京添煩添亂,而已。
從另一觀點看,結論也是一樣。江、胡交替之際,正是北京眼中香港對大陸的重要性大幅下降之時。九十年代,大陸經濟欲飛未起,江氏對特首有期望,要求這個人能把香港搞得比港英年代更好,不但讓國人揚眉吐氣,還能繼續帶動大陸經濟騰飛;因此,他更須要找一個懂得領導、高瞻遠矚有氣魄的人,於是找了董建華。
符合代際演化律
2000年後,大陸經濟已經走上大直路(發展經濟理論有所謂「turnpike theorem」,turnpike的引申義便是「大直路」,意謂發展中地區經濟一旦走對頭,上了大直路,自會風馳電掣,「想窮都難」,起碼到達中等發展水平為止),香港對大陸經濟而言,不再那麼重要,胡氏只須挑一個格局小一點的施政特首當爛頭卒便成。
胡重視特首上台之前的施政經驗,以及民望的質和量,因為那是當政後的政治本錢;起點政治本錢愈多,之後愈能花這種本錢為共產黨在香港幹「好事」。而且,只要肯幹這等「好事」並幹出成績,哪怕民望最後跌精光,對共產黨來說也是極好的,就怕一些港英時代舊電池做滿兩任特首一「事」無成而民望高企全身而退!
換句話說,特首的起點民望重要,因為有使用價值,終點民望並不重要,因為再沒有使用價值,太高了不僅是一種浪費,甚至還可能是有害的(特首民望如此拾級而下,實際上是數理控制論應用在胡所處的主客觀條件下的揀選特首,以及操控他辦「好事」的最優方案特徵,故此方案堪稱「胡氏優選法」)。
明乎此,港人萬勿捉錯用神,以為曾蔭權民望拾級而下,足令胡氏臉上無光,反映點錯了人;此觀點完全錯誤。怕自己揀的特首不成大器、令自己臉上無光的,是江澤民,所以當年才對着不識好歹敢問欽點的女港記一再駡街。胡不怕曾的民望下跌,因為那是要他多辦「好事」的必然結果,早已算入成本;他現時怕的是曾的政治本錢損耗殆盡卻「堵漏」不成。
江、胡上述分別,完全符合古今中外專制政權領導人的代際演化律:第一代是魅力領袖群,搞強人政治,以後的逐步失去特色,一蟹不如一蟹,最終只能「集體領導」。
第二代的習近平,時或說話令人則目,但不過是流露太子習氣,並非源於魅力和自信。觀其履歷,最亮點僅是受「負祖蔭」所累,文革時吃過一點黨內鬥爭的苦頭而已;這個妥協領袖,眼界胸襟難免比胡氏更低更小,受其他來頭更大的太子黨集團左右,上台後的政治行為勢必比胡更「不踰矩」。
再用「胡氏優選法」
明年初,若江已經不在,則習上台後,肯定沿用「胡氏優選法」挑香港特首,即在幾個政治及格的候點人當中,首挑民望最高、本錢最多那個;被點者須藉高民望盡力為共產黨在香港多辦「好事」,務求剛好在任內最後一刻把民望本錢有效消耗淨盡,無半點浪費;如此周而復始,五十年不變,直至「好事」做盡。期間,共產黨理性地不期望特首可於任內保持民望不大跌,因為那根本不可能。「胡氏優選法」因而是源於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期望論」(rational expectations theory)的中港政治版。
按此道理分析,目前已經浮出水面的幾位候點人,可得什麼結論呢?
論民望,范徐麗泰目前最高,但完全脆弱。這是因為她回歸後的民望不源於施政經驗,而僅僅來自主持立法會時的程式公正;這種公正,偏偏是她當上特首後,一天也不能維持的,因為當權少數派需要特首處事親疏有別,才能在「六四黃金律」之下保持此等少數派的實質當權地位。
如是者,范徐氏上任後的政治面目很快打回原狀,民望和親和力隨之化為烏有,其後能替共產黨辦「好事」的本錢遂等於零。她曾意有所指,提出下任特首必須推動「二十三條」立法,而自己只求當一屆特首為之「盡地一煲」,但此事她絕對辦不來,共產黨當然明白這個;這是她的致命傷。
唐英年的施政經驗量多而質低,兼乏基本政治智慧,以致近年民望從較高處滑落,不斷尋底,在關鍵的未來票源即年輕人當中,以他聲望最劣。若由他當特首,起點民望低,儘管有商界和中產擁躉,但總的來說,不比范徐氏優勝,試問又如何能有豐厚的政治本錢去花,扶正後替共產黨多辦「好事」呢?
至於梁振英,在商界有關係而無血緣,底子遠較唐氏薄弱,施政決策經驗掛零,共產黨委託他出任兩朝行會召集人自有原因,但如此「黨委」,依然不過智囊角色。打個比喻說,一個無駕照的人不知怎地當上教車師傅,坐在司機旁位指東點西好像頭頭是道,但並不等於他能開車,因為給意見和作決策,需要很不同、乃至相反的心理素質。
多年來,若梁氏願意,早可取得一官半職,累積不少決策經驗,但他通通回避,寧可誇誇其談天天出版大塊頭文章卻不幹實事,顯然信心有問題怕出錯。年來他扭盡六壬靠近民粹,試圖擺脫地產霸權利益分子色彩,但其背後最大支持依然來自地產界,洗底沒可能。論民望,他依然是共產黨在香港的一件負資產,一旦上台,社會馬上鬧翻天,遑論靠他替黨做「好事」;他根本一開始就沒有這個政治本錢。論優點,他意見多而智囊班底厚,最合當中策組首顧。
假如江澤民多坐一會……
結論是,若按民意本錢多寡定奪,北京心目中的理想特首還未浮現,最終找一個民望較高的前任或現任公務員、公職王或局長上位,遂大有可能,亦非太難。
當然,如果江澤民可以「多坐一會」,並且還能左右大局,則情況大不一樣。他依然會點一個他比較看得起、有多年決策經驗、高瞻遠矚、有魄力的人當特首,而且此人必須在起點上看起來比1997年的董建華還優秀,他才會認為有望擔起重任而不辱命。
上述三位候點人,一個也不入流。但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唐氏縱乏能力,以其施政經驗及講上海話的關係,獲點中的機會還是較高。若另有愛國愛港能人願意候點,則唐氏玩完。江決不希望再上演一齣「腳痛下台」劇;人脈關係斷不如身後名重要。
如果江澤民「不坐了」,則在此年頭時勢,最理想的特首——起點民望最高、胸無大志、卻願以一己政治本錢為黨做「好事」者,已經出現過,他就是曾蔭權。可惜,一蟹不如一蟹,似乎也是特區領導人的代際演化律。退而思其次,為黨辦「好事」,一人政治本錢不夠,可集多人,即搞「集體領導」。此說近日已然出現,並據說付諸實踐;而坊間流傳的「三位一體」論、「鐵三角」論,庶幾也是這個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