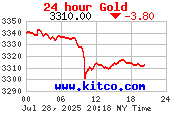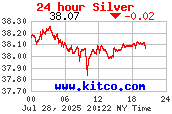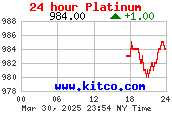黃元山
周三,聯儲局主席伯南克首次在議息後舉行記者會,希望增加運作的透明度。一般報道都覺得沒有太大驚喜,伯南克只是重複之前幾個月的論述:如重申他會如期完成QE2;不排除有QE3,但暫時看不到需要;否認QE引發了石油和食物的價格上升,認為油價只是反映供求關係,是短暫性的;他對美國經濟前景仍然只是審慎樂觀,就業和樓市仍然疲弱;預期寬鬆的貨幣政策會維持一段長時間;認為美元的弱勢只是短期的市場波動,長遠他支持強美元政策。
市場關注的,是伯南克是否會如期完成QE2和會不會推QE3,但較少留意到,其實他前天已經宣佈了QE2.5。回想去年初,第一輪QE大致完結,當時很多人預測聯儲局會退市,息率會飆升。不過,2010年8月,由於歐債危機越演越烈,伯南克宣佈了所謂的QE1.5,就是當債券到期後,會把回籠資金重新投資,使聯儲局所持的債券總量不變。當時QE1已經完結了,所以新一輪買債不算是QE1;但由於聯儲局所持的債券總量不變,所以也不算是新一輪的QE2。情況一直維持至11月,由於美國經濟實在太羞家,被迫要進行QE2。訴說歷史,是要說明之前QE1完結後,隔了半年,伯南克才推QE1.5;但今次QE2還未完,他已急不及待告訴大家會在QE2完結後,立刻開展QE2.5:把債券到期後拿到的本金重新投資,維持聯儲局債券總量不變。
QE3出台不遠矣
QE2.5已經來到,QE3還會有多遠呢? QE2.5的來臨,顯示了伯南克繼續實行寬鬆貨幣政策的決心,這個宣示,比任何議息聲明的字眼來得更實在更具體。雖然如此,美國政治現在風起雲湧,主要是針對民主黨政府是否審慎理財,可能會稍微拖慢伯南克印銀紙的速度。
2011年4月30日星期六
QE2.5淹至 美風起雲湧
2011年4月26日星期二
經濟過熱 中國2013年硬着陸
Nouriel Roubini
最近我先後兩次踏足中國,恰逢政府啟動十二五計畫,以重新調整其長期增長模式。而這兩次訪問,使我更加深信,中國的短期和中期經濟狀況之間,存在著可能影響穩定的潛在衝突性因素。
中國經濟目前已經過熱,但再過一段時間,當前的過度投資,將引發其國內乃至全球的通貨緊縮;一旦不斷增加的固定資產投資無以為繼─這很可能在2013 年發生─中國經濟的發展就可能嚴重放緩。
可見中國的政策制定者,應當關注的不是如何確保在當前實現軟著陸,而是經濟發展可能在五年計劃後半段,出現嚴重受阻的問題。
雖然新計畫也像上一個五年計劃那樣,宣稱要增大消費佔GDP 的比例。但對政府來說,政治阻力最小的做法依然是維持現狀。公開發布的新計畫細節也顯示:經濟的增長依然要仰仗投資(包括興建公共住房)來支撐,而不是以實施更迅速的貨幣升值,面向家庭的大規模財政轉移支付,稅收和/或國有企業的私有化,解除戶口制度限制以及放寬財政管制的方式來實現。
過去幾十年以來,中國都是靠以出口為導向的工業化和弱勢貨幣來實現增長,並因此催生了極高的企業和家庭儲蓄率,以及對淨進口和固定資產投資(基礎設施,房地產以及來料加工和出口部門的生產能力)的依賴。
當淨出口金額從2008 至2009 年度的佔GDP11%,下降到5%的時候,中國領導人的應對措施,就是將固定資產投資占GDP 的比例從42%拉高到47%。
憑藉著爆發性的固定資產投資,中國得以擺脫了2009 年日本,德國和亞洲新興國家所遭遇的嚴重經濟衰退。但固定資產投資佔國內GDP 的比例,也因此進一步上升到2010 至2010 年度的近50%。
這就暴露出一個問題:任何國家都不可能擁有足夠的發展速度,足以在將50% 的GDP 重新投資的情況下,最終避免遭遇巨大的產能過剩,和令人憂心的不良貸款問題。中國內部到處充斥著在實物資本,基礎設施和不動產方面的過量投資。在一個訪問者眼中,證據就是那些光鮮靚麗卻旅客寥寥的機場和高速列車,通往偏僻之地的高速公路,數千座高大的中心城鎮和地方政府建築,空無一人的新城區,以及被迫關閉以避免引發全球價格下跌的嶄新鋁冶煉廠。
商業和高級住宅方面的投資早已過剩,汽車的產能即便在最近的銷售熱潮中也已經過量了,鋼鐵,水泥和其他製造部門的產能過剩問題也在不斷惡化。在短期內,這場投資繁榮將刺激通貨膨脹,這是源自于其高度資源密集型的增長特點。但過剩的產能將無法避免地帶來嚴重的通貨緊縮壓力,而製造業和房地產部門則首當其衝。
中國大概會在2013 年後遭遇一場硬著陸。事實上所有與過度投資有關的歷史場景─包括在1990 年代的東亞地區所發生的一切─都會以一場金融危機和或長期的低增長來謝幕。如果要避免這一命運的話,中國需要降低儲蓄率,減少固定資產投資,削減淨出口佔GDP 的比例,並刺激消費所佔的比重。
但問題是中國人之所以樂於儲蓄而不願消費,是有其結構性原因的。而要扭轉這一過度投資的誘因,可能需要整整20 年的改革。
對於高儲蓄率的傳統解釋(缺乏社會安全網,有限的公共服務,人口老化,消費信貸的不發達),只是這一迷局的其中一部分。中國大陸地區的消費者並不比香港,新加坡和臺灣等地的同胞更傾向于儲蓄─他們都同樣會將大概30%的可支配收入存起來。但最大的區別在於家庭部門佔中國GDP 的比例小於50%,因此也只給消費留下了一個很小的空間。
人民幣弱勢保護出口
中國實施的一系列政策,都是將大量收入從政治上處於弱勢的家庭轉移到了強勢的大企業手裏;弱勢的人民幣使進口商品變得昂貴,降低了家庭購買力,卻保護了那些出口型國企並增加了出口商的利潤。
面向家庭的低存款利率和面向企業和開發商的低貸款利率,意味着千家萬戶的巨額儲蓄實際上的是在賠錢,而國企的貸款成本卻是負數。這就產生了一個強大的過度投資誘因並意味著從家庭向國企的大規模轉移支付─倘若這些企業以市場利率貸款的話,肯定是要虧損的。
此外,對工人的壓榨,也導致工資上升的幅度,遠遠低於生產力的增長速度。
如果要放寬對家庭收入的限制的話,中國必須讓人民幣更快地升值,放開利率管制,並大幅增加工資。更重要的是,中國要麼必須將其國企私有化,讓這些企業的利潤能轉化為家庭收入,要麼像這些企業徵收更高的稅收並將這些財政收入轉移給家庭。事實上,除家庭儲蓄之外,企業部門(大部分為國企)的儲蓄─或者說保留利潤─已經佔到了GDP 的25%。
但增加家庭佔總收入比例的舉措,將產生極大的破壞效應,因為這會導致一大批國企,出口企業和地方政府破產,而這些又是在政治上很有權勢的部門。最終導致的結果,就是中國只能在這個五年計劃中,繼續增加投資。
繼續沿著這條投資導向的道路走下去,將使已經暴露出來的製造業,房地產和基礎設施產能飽和現象進一步惡化,並將在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無法繼續擴大的情況下,加劇未來的經濟放緩。但直到領導層在2012 至2013 年換屆之前,中國的政策制定者們,都將繼續在罔顧巨額未來成本的情況下維持一個高增長率。
作者為魯賓尼全球經濟研究院(www.roubini.com)主席, 同時也是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教授以及CnisisEconomics 一書的合著者。
Is China becoming Japan in the 1980s?
Let's talk about a boring topic today – China's inflation.
Even if you have only paid scant attention to economic news, you have probably noticed that the topic of rising prices in China has come up again and again in the media. Indeed, for the past year, it has been a grave concern for Beijing to tame inflation in the country .
The latest economic data released last week didn’t ease the concern.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 (CPI) surged 5.4 percent in March from a year ago – higher than the 4.9 percent in February and market consensus of 5.2 percent – indicating a worsening trend.
So it comes as a remarkably contrarian voice when somebody suggests that China could be heading toward deflation, instead of inflation. Especially if it comes from the prescient Dr Nouriel Roubini, you'd better take heed.
In his usual alarmist manner, Dr Roubini, nicknamed Dr Doom, said in his article “China’s Bad Growth Bet” that China’s “current overinvestment will prove deflationary both domestically and globally” over time. He is predicting this will happen most likely after 2013 and China is “poised for a sharp slowdown”.
His rationale is simple – the level of investment in China is unsustainable and will backfire eventually. China always has a high level of investment but it got even higher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As China struggled to maintain its near double-digit GDP growth rate after the crisis, it boosted its fixed asset investment to fill the void from collapsing trades. The share of fixed investment in GDP has risen to nearly 50 percent this year from just 42 percent before the crisis. As Roubini rightly pointed out, no country, even China, would be productive enough to reinvest half of its GDP without facing enormous overcapacity and non-performing loan problems. Such worry is not groundless. In fact, we can find striking similarities between China now and Japan in the 1980s.
As a result of heavy lending and inflated asset prices, investment accounted for a large share of GDP in Japan during the 1980s. The figure was 31 percent in 1988-1990, already a pretty high figure, but China’s figure is still much higher.
Both China and Japan have relied on export-led growth. With the strong surplus in the external accounts, their currencies should normally appreciate. But for whatever reason, both governments have tried to hold down their currencies by explicit or implicit interventions. The result is massive foreign currency reserves and asset bubbles due to the liquidity injected into the system through currency interventions.
Bank loans were also pivotal in driving investment booms in both countries. Bank lending was growing faster than nominal GDP growth for both of them. What made things worse was that lending decisions were not based solely on commercial merits. In 1980s Japan, you had zaiteku, which means “raising profit by utilizing capital for securities investments, real estate and the like”. Intercompany loans between related companies allowed companies that otherwise would not have easy access to bank credit to borrow money cheaply. As real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ran out, money flowed into real estate and other asset markets, fuelling bubbles.
A similar scenario is starting to surface in China.
Some would argue that China’s GDP is still growing strongly so we should not get caught up in the scaremongering tactics of those doomsayers. The strong growth of GDP, however, is precisely the reason why an eventual collapse seems inevitable. As investment now accounts for nearly half of China’s GDP, the repercussions could be huge when those investments turn sour. China’s obsession with GDP may prove fatal when people realize the money that has been spent during the boom years went into building bridges to nothingness or ghost towns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Perhaps w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ears the most is not the country will turn into Japan in the 1980s but rather into itself in the 1980s. Driven by market-liberalizing policies, China enjoyed strong economic growth in that decade. But high inflation, like current one, plagued the whole country. Inflation spiked to nearly 20 percent in 1988 and 1989 before dramatically falling to 2.1 percent in 1990. Well, we all know what happened in 1989, don't we?
Jacky Wong is a Hong Kong-based analyst. He has worked at global investment banks and hedge funds in various roles including derivatives trading and equity research.
2011年4月22日星期五
本港樓市將近見頂
2011年4月5日星期二
2011,我們的日子還會這麽難嗎?
郎咸平
2011年年初,我推出了新書《郎咸平說:我們的日子爲什麽這麽難》,上市之後得到了很多人的關注,反響很大。《人物》 雜誌從讀者中徵集到了一些問題,希望我的回答能解決更多讀者心中的疑惑。
《人物》:您曾說過,中國人全球工資最低。但當有人建議給大家發工資時,便有專家說可能會導致通貨膨脹,這兩者之間有關係嗎?現在超量的貨幣有否體現在個人收入的增加上?
我:那些專家是照搬教科書上的理論:每年經濟産出就這麽多,比方說就100斤大米,而工資如果是100塊,那麽米價就在一塊錢一斤,這樣,工資如果漲到了200塊,大米還是那麽多,所以物價是兩塊錢一斤。這個理論放在歐美基本上是對的,因爲那些國家工資占GDP的比重非常高,這樣你漲工資等於沒漲,因爲東西還是那麽多,越漲工資,錢越不值錢,這樣會有通貨膨脹。
這理論的前提條件是什麽?國民經濟的大部分産出都被工資消費掉了。但是,中國的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是全世界最低的,就算老百姓工資翻一番,其對通貨膨脹的影響力也不及政府舉債投資的五分之一,也不如天量信貸的十分之一。你想想看,我們的産能過剩這麽嚴重,各行各業都是嚴重的供過於求,而且什麽都漲,就是工資不漲,按照這些專家的理論,怎麽可能發生通貨膨脹呢?可是現實又如何呢?去年我提出警惕滯脹這個觀點的時候,還有某個經濟學家和我辯論,可是,現在連他自己都修改了自己的觀點。
《人物》:您特別主張藏富於民,您認爲主要應該通過何種路徑來實現藏富於民?
我:我最近提出一個“馬車理論”。企業投資和個人消費是國民經濟的兩匹馬,政府拿著稅收這條鞭子在駕車。現在情況是,國企不去拉車反而在車上增加負擔。政府不去養馬,反而用越來越重的鞭子加重負擔。2009年,財政收入和國企利潤占了GDP的35%。企業各種稅負有20多種,占稅前利潤的70%,全世界最重。以個人養老金爲例,薪水的8%要上交到個人養老金賬戶,同時企業要再交20%到社會統籌賬戶,這麽高的繳款比例卻並不是因爲真的給老百姓養老了,而是因爲養老金既有歷史漏洞,又有統籌和管理成本過高、投資收益過低這一系列問題。換句話說,稅收本來是再分配的過程,可是我們的稅收卻是收上來就完了,不是真正給老百姓花錢,不是公平地再分配給老百姓。藏富於民就是要減輕企業和個人負擔,讓國企不再利用壟斷地位與民爭利。
《人物》:當貧富差距擴大,社會矛盾便會突出。您曾說窮苦人群開始絕望了。您認爲這種情況發展下去,是否會形成政治風險?應該怎樣避免這種風險?
我:我看到社會上更多的是無奈而不是絕望。
我最擔心的不是什麽政治風險,而是老百姓過得幸不幸福。央視每年進行“經濟生活大調查”,有一題是您對目前生活的感覺:很幸福、比較幸福、一般、很不幸福。其中選擇很幸福的比率一直是4%左右。選擇不幸福和很不幸福的比率在不斷上升,2007年18%,2008年24%,2009年是25%。今年達到38%。調查顯示不幸福的原因主要是對收入和住房不滿意。
順應民意就不會有政治風險。比方說2006年的結果顯示老百姓最關注的是醫療。隨後我國進行了醫療改革,現在連普通農民都能報銷60%的醫藥費。儘管還有很多問題,但是老百姓對這方面的滿意度至少提高了一點。
《人物》:金融危機使西方人極大地克制自己的消費行爲,而在中國似乎影響不大,2008-2009年的餐飲娛樂業並不蕭條,這是爲什麽?還能說中國人工資低嗎?
我:美國老百姓不是克制消費,而是因爲過去濫用消費信貸、過度透支,現在失業率還居高不下,當然消費不振。金融危機是怎麽來的呢?就是本來一個人買不起房子,但是銀行借給你錢讓你買。因爲房價一直在上升,過了兩年之後,房價升值這部分銀行還給你辦理再貸款,升值這部分就變成消費貸款給你繼續揮霍。
中國情況與此完全不同,中國目前正在走向M型社會,窮人富人同時增多,中産缺失。餐飲娛樂行業不蕭條很正常,因爲有錢人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但是普通百姓的娛樂並不見得有多麽繁榮。以電影院爲例。我國每10萬人擁有的銀幕數是0.41塊,美國是12.7塊,差距達30倍。 M型社會下層工資低是客觀事實,餐飲娛樂蕭條不蕭條和他們沒有直接關係。你判斷中國餐飲娛樂行業不要只看到北京上海,你去三四線城市和小縣城看看小飯店幾點打烊就知道了,那裏住著的才是大多數的中國人。
《人物》:由於文化傳統和投資渠道有限的影響,中國的個人儲蓄不斷增加,這會對中國的經濟發展産生怎樣的影響?是否需要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通過拓寬投資渠道嗎?在中國大陸能否出現切實保證個人投資利益的投資渠道?投資現在的股市會有很大風險嗎?
我:我很同情我們老百姓,在中國我也不知道建議他們幹什麽。投資黃金,現在漲得離譜;炒外匯風險很大;投資股票,到處是內幕交易;辦企業,稅負超過稅前利潤的70%。投資房地産,現在政府天天在限制。現在想想美國老百姓活得真簡單,買基金或者存入自己401k養老金賬戶就行了,政府負責他保值,替你看管錢。我們到頭來是政府提供不了一個好的投資環境。
個人儲蓄增加實際上是個僞命題。個人儲蓄的增長速度遠遠比不上企業和政府。從1992到2007,家庭儲蓄占GDP比率一直在20%,增長率爲0。企業儲蓄占GDP比例從11%增加到23%。政府儲蓄從GDP4%到8%。增加的儲蓄是企業和政府的。
即便如此,還有專家抱怨我們存款過多,說要鼓勵消費。這完全不理解我們老百姓的日子有多苦,而且因爲社保、醫改、教改和房改都沒能切實減輕老百姓的負擔,所以老百姓越窮越不敢花錢,這個已經被尼爾森公司的調查資料證實了。所以,我請這些專家和政府不要再打老百姓那點儲蓄的主意了!儲蓄根本就不是個問題,因此無從談起怎麽解決,問題在於怎麽藏富於民。
《人物》:謝國忠說未來十年會進入通脹時代,您是怎麽認爲的?如果真的進入十年通脹,將會是怎樣的情景?
我:中國當前的問題不是通脹這麽簡單,是滯漲。我早在幾年前就指出過這個問題,所以才大聲疾呼反對四萬億。滯漲是說,經濟高增長已經不可能了,通貨膨脹同時出現。要治理通脹就要收緊流動性,加息、提高準備金率,控制貸款等,無疑這會更加打擊經濟。如果要提振經濟,就要放寬流動性,通脹壓力又會增大。
《人物》:您對目前的“公務員熱”怎麽看?大學畢業就做“蟻族”是因爲社會提供的就業機會太少還是報酬太低?
我:根本原因是社會上年輕人沒有機會。公務員熱是因爲他提供了一條穩定的就業渠道。這和超女、超男的火爆是同樣的原因,選秀爲年輕人提供了成名的機會。
《人物》:央行年內6次增加存款準備金利率,這是最有效的手段嗎?是中央政府最重要的遏制通貨膨脹的方法嗎?
我:這是最典型的“頭疼醫頭腳疼醫腳”。 提高準備金率是爲了收回資本金,但是同時我們卻大放信貸:2010年前11個月新增貸款7.45萬億,2007和2008年的總和才8.4萬億。另一方面是地方債,最保守估計7.6萬億。這麽多錢放出來,收點幾千億的流動性能起到遏制通脹的作用嗎?
《人物》:有種共識,認爲中國房地産行業如此增長與地方政府的支援密不可分。僅僅是爲了追求GDP、地方稅收增長、官場業績?還是由於腐敗?或者說其中哪種原因更爲重要?
我:你知不知道買房的人對社會有多大貢獻?2009年全國土地出讓金1.6萬億,你知道這意味著什麽嗎?按照陝西神木縣全民醫保的標準40萬人,每年報銷1.5到1.8億元,以1.8計算每年只需5850億就能實現全民醫保。按照規定把土地出讓金的10%用來建保障房,每平米1500元高標準建造,可以建1億平米。2009年我國住宅竣工面積不過5.77億平米。這樣還剩下八千億元,你可以讓全國的高中和大學教育都免費。 換言之,每年的土地出讓金足夠讓老百姓享受免費醫療、廉租房、十二年免費中小學教育和大學免費。
問題在於,我們把房地産收上來的錢幹什麽用了,沒有人知道。這不是房地産的錯,也不是買房人的錯,是我們的財政體系不問責,不透明,不公平。現在又要開徵房産稅,似乎就是把房價問題都歸咎于買房的這些人,但是你仔細想想這究竟是誰的責任呢?
《人物》:重慶對高檔住宅開徵房産稅,您對這一舉措有何看法?
我:2009年徵收了1.6萬億土地出讓金,占地方收入的一半。仍然想征房産稅,沒有道理啊。我們一直沒搞懂,房産稅的本質是讓房子增值,而不是用來遏制房價的。
而值得注意的是重慶模式並不只是對高檔住宅開徵房産稅這麽簡單!這背後需要一系列的系統工程,如果沒有這個系統工程,而只有房産稅,那麽就是錯誤的。這個系統工程首先大規模建保障房,低價出租保證居者有其屋。而且要設計得很巧妙,這些房子將來要賣也只能賣給政府,這樣“寬進嚴出”才能保證真正有需要的人入住。
《人物》:當年的“分稅制”使中央財政極大增長,爲之後的快速發展提供了很大的保障。現在地方財政減少使得地方政府又採用大量政府融資的方式來保證地方經濟的發展,但是這又會産生極大的風險。如何改變這種與分稅制之前相反的中央地方財政狀況?靠轉移支付能行嗎?還是再取消分稅制?
我:什麽是經濟發展,靠地方融資或中央投資來保證經濟發展就是個錯誤命題。八九十年代我們基礎設施不完善,修公路鐵路、搞工業園發展外貿經濟是沒錯的。現在基礎設施已經很完善了,地方還在花大力氣修産能過剩的高鐵和機場,這條路已經走到頭了。經濟發展是靠企業投資和個人消費帶動的。比如今年經濟體有100元産出,政府拿20塊錢就足夠了,這個不是用來三公消費或者走老路,而是應該投入醫療、教育、保障房,讓窮人分享發展的好處;餘下40塊留給企業擴大再生産,多雇人,漲工資;40塊錢留給老百姓消費,這樣自然會走向內需型經濟。從長遠來看,真正能保證經濟發展的不是地方政府的低效投資和政績工程,而是企業一直有足夠的利潤進行研發和投資再生産,老百姓一直有足夠的消費能力購買這些産品。
稅的核心不是怎麽收錢,而是怎麽有效地花錢。目前問題不是取消分稅制,而是加大問責制。需要花錢了,提出預算,每一筆錢怎麽花,然後收稅。你要清楚地告訴百姓你的錢花在了哪里。只要花錢不透明,錢怎麽都不夠用,無論是分稅制或者地方債都是不是問題的本質。
《人物》:您曾說美國高盛是導致金融危機的一大罪魁,一家投行的影響真的有那麽大嗎?您如何看待高盛現在在中國金融市場的作爲,對與他們合作的中國資本您有什麽話要說?
我:高盛不是一個人在戰鬥,他代表的是美國的金融資本,他們彼此分工、互相合作。我們揭露高盛不是爲了批評這一家公司,而是想讓大家警惕美國金融資本對我們的傷害和操控。
當然高盛是這些公司中的佼佼者。我以這次歐元危機爲例,2001年希臘希望進入歐元區,但是他達不到歐盟的兩個標準,預算赤字不能超過國內生産總值的3%、負債率低於國內生産總值的60%。高盛爲希臘設計出一套“貨幣掉期交易”方式,爲希臘政府掩飾了一筆10億歐元的公共債務,還將國家彩票業和航空稅等未來的收入作爲抵押換取現金。高盛知道希臘將來必然會有問題。因此高盛便向德國一家銀行購買了20年期的10億歐元CDS“信用違約互換”保險。一旦希臘政府出現支付危機,出售CDS的銀行就要支付高盛10億歐元的虧空。
隨後華爾街對沖基金坐等歐元危機爆發,從中漁利。2010年2月,歐元淨空頭6.3萬手,看空力量是看多力量的5.5倍。爲什麽這些對沖基金對歐洲的情況這麽瞭解?因爲高盛知道了。
能夠把歐洲的主權國家玩弄於股掌,至少這樣的對手值得我們警惕。
《人物》:您對食品安全、環境污染也特別關注,連地溝油、垃圾處理等微觀問題都進行了深入研究,這是基於何種考慮?
我:這些問題的本質是政府監管缺失,這些問題的根本是百姓利益受損,我做這些是因爲我想爲老百姓說話。
所謂的宏觀調控到最後都是一個個微觀問題。我一直呼籲“藏富於民”,這不僅僅是讓老百姓有錢了,還包括過一種體面的生活:吃放心食品,呼吸新鮮空氣也是我們的權利。這些都是一個學者起碼的良知。
《人物》:2011,我們的日子還會這麽難嗎?
我:答:2011是十二五開局之年,而十二五計劃第一次將”擴大內需“獨立成篇,這與我一直呼籲的”放棄保八,藏富於民“的主張是非常契合的。但是正如我在書中分析的,我們不是沒有意識到”看病,上學,買房“成了新的三座大山,實際上,我們也沒少採取措施來應對這三個問題,可是,房價卻是越調越高,老百姓對上學難和看病難的抱怨也還是不少。這背後缺失的是我們並不瞭解這些問題的本質,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因此,我作爲一個學者一再給大家講解”重慶模式“,就是希望大家能夠明白房價太高的根源在哪里。同樣,對於醫改,我注意到有計劃在十二五期間自付醫療費不超過三成,但是我們總是有太多計劃,太多目標,當然,我希望這些美好的目標都能實現,這樣老百姓的日子才不會這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