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五常
雷公老弟鼎鳴七月十九日在《信報》發表《中國應嚴厲打擊學術腐敗》,是做過功課才動筆的文章。該文指出神州大地學術腐敗成風:抄襲、冒牌、研究弄虛作假、論文槍手生意滔滔。沒有理由懷疑他的報導,問題是如果這些「腐敗」行為一律清理得一乾二淨,中國的學術會搞起來嗎?賭搞不起來我敢賭身家。
關鍵在學術氣氛
鼎鳴老弟是把問題本末倒置了。學術發展的氣氛能成功地搞起來,上述的「腐敗」不打自散。學術氣氛搞不起,管制得怎樣嚴謹也不會有作為。印名頭,數文章,論學報,大學的君子們不是為了好奇心而做學問,不是為了興趣而追求,只是為米折腰,或為米出術!這樣,在國際學報上發表無數文章,篇篇不「腐敗」,寫得規格井然,但味同嚼蠟,沒有令人驚喜的新意,缺少了啟發力,傳世的機會是零,有什麼意思呢?
在學問爭取的歷程上我比鼎鳴老弟早出十多年,享受過大約十年的西方學術的黃金時代。越戰開始後不久一切都在變,變得快,到了七十年代後期,先進如美國,學術氣氛是明顯地減弱了。想當年,無論在母校洛杉磯加大,或長灘大學,或芝加哥大學的幾個學院,或七十年代初期的西雅圖華大,同事之間坐下來談的一定是學問上的話題,學生進入教授的辦公室一定是要研討學問。這情況跟我一九八二年回港任教後遇到的是兩回事。神州大地的現代學術發展起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受到的外間影響是壞影響!
當年在美國,銜頭不重要。我自己差一點因為要多付五十美元而不拿博士文憑。一張紙要來作什麼?當時《佃農理論》寫好了,沒有誰管我是不是「博士」。芝加哥大學邀請我到那裡時,作為系主任的夏保加說得清楚:有沒有博士不重要。當時芝加哥經濟學派的一個重心人物——戴維德——不是博士,學士不是唸經濟的,只發表過幾頁紙的文章。我拜服戴老是遠在到芝大之前:一九六三年初聽到老師阿爾欽介紹戴老的綑綁銷售的口述傳統,著了迷,啟發了我三年後動筆的佃農理論。一九六八在芝大,科學院的院長基爾.莊遜對我說:有沒有文章發表不重要,重要的是思想有深度,以口述表達出來也是可以的。
想當年,從來沒有人問及我求學時的考試成績:找大學教職主要是教授或同事們的口頭推薦。也是作學生時,選修科目不需要管哪種科目有較佳出路。選自己有興趣的,也選教授的學問斤兩。這一切後來逐漸轉變,七十年代後期轉得快,八十年代中期起,什麼學術云云不知從何說起。如果六十年代的學術氣氛像今天的,我不會選走學術的路。
學者追求抽象回報
我說的學術——鼎鳴老弟關心的學術——主要是思想的發展。通常是抽象、軟性的學問,產出的作品一般沒有直接的市場價值。學生出錢求學是學怎樣思想。薪酬不足道,學者的回報主要是好奇心的滿足感,同事之間的互相欣賞,以及有機會傳世的驕傲。這裡說的思想是概念、理論、假說、驗證,要講深度,論新意,重啟發。大學是為了這些學問而設的:本科教基礎,研究院學創作。不限於實證科學。當年讀歷史,讀藝術,有道的老師教概念,教理論,所有學系都歸納在哲學的範疇內。知識理論與邏輯、倫理等皆屬哲學系的教材。當年大家知道哲學系最難讀,也最受尊敬。今天,一個哲學大師是不容易找到飯吃的!人浮於事,為米折腰,換來的是沒有誰再純從興趣來處理那些沒有直接市場價值的思想作品。我不懷疑鼎鳴老弟對今天的味同嚼蠟的所謂國際名學報的文章比我重視得多,但老實說,如果當年的學報題材與趣味像今天這樣,經濟學不會有我這個人。是他們遺棄了我,還是我遺棄了他們呢?是二者的合併吧。
不久前在芝加哥大學舉行的一個研討會中,參與的朋友傳來兩項使老人家開心的信息。其一是諾斯三番幾次對人說,經濟學他從我那裡學得最多。是陳年舊事,記不起是他教我多還是我教他多。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當年的經濟學像今天這樣,地球上不會有諾斯這個人,更勿論他的諾貝爾獎了。當年在華大,諾斯與巴澤爾從來不問我有沒有文章發表,也不問我教什麼,只是每隔幾天問我在想什麼。他們站在旁邊不斷地拍掌,鼓勵我寫下些今天還有人讀,還常被引用的文章。如果當年我要受學報編輯或評審員的氣,這些文章不會寫出來。說得清楚一點,我當年的英語文章是同事們拍掌拍出來的,所以今天還傳世。
中國奇蹟在古文化復興
芝大研討會傳來的另一個信息,是一位參與的朋友說,聽到的評語是新制度經濟學推我這個老人家為首。是賣不到錢的學問!是相對的,我跑出主要因為沒有幾個人真的跑——沒有幾個重視真實世界的局限——而我是加上得到中國經濟改革的啟發。說過了,回港任職後轉用中文動筆是對的選擇,可以寫得多,寫得快,可以更為自由地發揮,有了思想發展的大概才有系統地回頭整理。後者是今天老人家的工作了。
今天回顧,我的中語文章比英語的約多四十倍,更為粗略的估計,學問思想的貢獻約三倍。幾位知情的朋友認為,只要神州繼續再起,有朝一日中文在國際上受到重視,找老人家的抗衡對手老外要回到斯密那頭去。一九八一年我不是準確地推斷了中國會走的路嗎?以中文動筆不是有先見之明嗎?以中文動筆不算是學術是香港的有趣發明,但也只不過是為米折腰的無聊玩意罷了。說不出一句有啟發性的話,用什麼語文動筆也同樣無聊。腐敗要怎樣算才對呢?
歷來欣賞中國人的天生基因,佩服中國詩人的想像力,驚嘆中國的古文化。論思想,孔夫子那個時代了不起。後來學而優則仕的發展提供了一個管治成本低廉的制度。這制度對工業發展不利,加上西方入侵帶來的悲劇起於鴉片戰爭之前。二百多年的風風雨雨,代價或成本無疑龐大。今天,中國的經濟奇蹟使舉世嘩然。歷史成本再不是成本,我們要向前看。
說過了,人類歷史上沒有一個古文化可以在凋謝之後回頭再起。這樣看,中國最大的奇蹟不是經濟發展,而是一個龐大無比的古文化正在復興。關鍵問題是:如果中國的學術像今天那樣,搞不上去,正在復興的文化早晚會再倒下來。歷史的經驗說,文化的興起要靠經濟支持,而文化不振大好的經濟發展不會持續。學術發展是文化發展的命脈所在。
學術桃花源絕不仁慈
對教育與研究的資助,北京是慷慨的。困難是中國的學術思想發展的成績有很大的一個問號。雷鼎鳴指出的腐敗現象,是失敗的效果,不是原因。遠的不易考查,我認為北京的朋友要好好地研究一下英國及美國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學術制度,選幾間有大成的學府為範。這些年中國引進西方的經濟制度或政策頻頻失誤——中國的經濟發展有成主要是靠自己想出來的制度或政策。學術上,引進西方七十年代後期開始的數文章、論學報的準則是錯誤的選擇。我認為早一段時期西方的學術制度,擇其善者而效之是明智的。就算完全不考慮西方曾經有過的上佳學術制度,發明自己的總比今天抄過來的為上吧。
回頭說上文提到的上世紀中葉西方的學術桃花源,可不是個仁慈的地方。當時的學術有英雄,也有敗將,而好些學府之內勾心鬥角的行為時有所聞。學術競爭也有代價。這是後話,按下不表。
-------------------------------------------------------------------------
雷鼎鳴
中國應嚴厲打擊學術腐敗
今年二月八日拙作《未來三十年的中港博弈》曾指出,以GDP而論,香港經濟佔中國經濟的比重愈來愈微不足道,這個趨勢難以逆轉。
我多年來一向認為,香港經濟要向前發展,必須同時做到兩件事,一是融入中國經濟,二是要不斷搜尋及發揮香港「無可替代」的相對優勢。香港相對於內地,有什麼獨特性及優勢?各行各業要自己找出答案。
近年內地、香港及國際的媒體有不少關於內地學術腐敗的報道及議論,可再次提醒我們,香港的優勢之一正是它的學術界比內地純潔得多,這項優勢必須延續。內地出現了什麼樣的學術腐敗及造假?它們會帶來什麼後果?我們可先從最近已成公共議題的汪暉「抄襲門」事件說起。
學者抄襲普遍
汪暉是內地新左派的思想領袖,當過《讀書》主編,現任清華人文學院教授,成名作是在一九八八年答辯、一九九○年出版及後來多次再版的博士論文《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
今年三月十日及二十五日,南京大學的王彬彬教授先後在《文藝研究》及《南方周末》刊登長文,指出《反抗絕望》中有十二處四千多字的內容,涉嫌抄襲了四位海內外學者的五本著作。
王彬彬文章刊後,「汪粉」(汪的支持者)及以「打假」為己任的網民互相對陣,爭吵不已。有幾位學者願意替汪說話,但認為,他大有問題的亦不在少數。汪從前的博士論文委員會成員嚴家炎如此評價:「王彬彬先生文章中摘引出來的地方,確實證明王暉與他人有多處文字基本上相同,卻完全沒有注明出處,前後也沒有說明交代,用了一段跟別人幾乎不差幾個字的文字,你說這個部分是抄襲或變相抄襲,我覺得可以說。」美國兩位著名學者,威斯康辛大學的林毓生及普林斯頓的余英時對此事意見一致,林在六月六日《南方都市報》評論周刊的訪問文章中表示震驚,同意嚴家炎對事件的評估,並嚴厲批評抄襲是侵害別人知識產權的失德行為。
林毓生與余英時都認為,清華的文學院院長及校長「有政治及道德責任盡速成立『汪暉涉嫌抄襲調查委員會』」,若不成立,院長與校長都應下台!我問過清華的朋友,他們都未聞有為此事成立了什麼委員會。
汪暉自己並無出面申辯,但在媒體上可看到其擁護者的一些辯解,卻使人哭笑不得。例如,有人引開話題,反而批評王彬彬多管閒事,沉迷於要充當「引注規範」的「糾察員」。有人又質疑西方學術界的學術規範(指引用別人成果時要說明出處),認為它會成為思想大師的羈絆。
林毓生更發現,有人認為「抄襲幫助他(汪)節省了時間,把主要精力放在他的理論建樹上,他借抄襲才變成有世界水平的學者」。這類不值一駁的奇談怪論,在神州大地俯拾即是。
CEO虛假學歷
學術腐敗的另一形式是虛報資歷。近日被揭發的微軟中國前CEO「十億打工皇帝」唐駿,他的博士學位原來不是加州理工所頒,而是由「文憑工廠」野雞大學所發。
我自己便認識一位仁兄,此人的學歷及工作經驗,看來樣樣光芒耀目,但幾乎全部虛假。此君回到中國後,神通廣大,在某些機構工作一段時間後,真身暴露,卻居然又能轉到別處,繼續其行騙生涯。最近在網上發現他竟當上了一所大學商學院的院長,而且在媒體中頗為活躍,不到你不服!
但虛報資歷的行為,嚴重性卻又遠遠不及偽造科學資料。偽造資料會誤導其他研究人員,把科學研究引入歪路,浪費資源,拖慢經濟發展。
據今年一月十二日國際科學界兩大頂尖刊物之一的《自然》(Nature)報道,武漢大學及清華大學兩項獨立的調查都發現,大約三分之一被訪內地研究者都承認,曾經抄襲或偽造過學術資料。
去年底英國一份結晶體的學術刊物便決定撤回井崗山大學一些研究人員在該刊出版過的七十篇論文,因為發現資料都是虛假的。這所以革命聖地為名的大學,其聲譽所受的打擊嚴重程度可想而知,但校方只是開除了其中兩位學者,其他作者的收場如何,仍未知曉。
事實上,從《自然》及其他國際期刊對中國學術腐敗的多次報道看來,中國的大學對「打假」的責任,通常都是敷衍了事。
中國「打假」不力,其他國家又如何?近年幾次國際上有名的「打假」行動中,我們可看到麻省理工、東京大學及首爾國立大學等著名學府都能迅速成立調查委員會,明快果斷地找出真相,毋縱毋枉地把事情處理好。最有代表性的一次「打假」是○二年貝爾實驗室對德籍青年物理學家桑恩(Jan Hendrich Schon)的調查。
桑恩一九九七年在德國康斯頓大學(University of Konstang)取得博士學位後,便到貝爾實驗室工作,研究納米科技。在短短幾年內,他在頂尖期刊出過近百篇論文。
在二○○一年,他的速度是每八天出一篇,而且是在最權威的刊物。他迅速冒起,連奪大獎,被視作可獲諾獎的神童,在超導體,分子半導體都被認為有突破性的發現。可惜,他的實驗結果原來都是子虛烏有。他名聲鵲起後,別人想複製他的結果,但無人成功,慢慢他便露出馬腳,促使貝爾實驗室徹查此事。
外國嚴打抄襲偽造
貝爾實驗室當時有財政困難,正在承受著巨大的早日要出科學成果的壓力,桑恩事件若屬實,實驗室的形象會大受打擊。但實驗室卻選擇勇敢地調查,這位明星學者在二○○二年分別致函給刊登過桑恩論文的期刊,告知它們資料都是虛假的。它的高級副總裁寫道:「我們對科學的榮譽操守極為重視。」二○○二年《科學》決定撤回了桑恩的八篇論文。二○○三年《自然》也撤回了七篇。但最值得鼓掌的,卻是桑恩的母校。
二○○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自然》的社論報道,康斯頓大學決定褫奪桑恩的博士學位,並在聲明中說:「他濫用了這張進入學術世界的入場券(指博士學位),而且所用方法是如此存心不良及不負責任,他放棄了對學術的獻身,博士學位的尊嚴受到危害,……科學在公眾眼中的公信力被破壞。」洋人對學術腐敗立場如此鮮明,中國學術界卻是首鼠兩端,一部分人甚至要把它合理化,要學術規範走所謂「中國模式」,這如何對得起堅持學術操守的研究人員?
為什麼學術界對學術腐敗必須採用十分嚴厲的態度?這問題有經濟學的解釋。學術界大部分的基礎研究成果都只是對公眾可能有貢獻,對個別的公司作用有限,所以公司不大願意出錢負擔學術研究的費用,學界中人的收入回報與其付出的代價及時間相比,其實十分菲薄。
支持他們工作的動力,是來自其求真精神及發現新事物的樂趣。若有害群之馬出現,殃及池魚,使自己辛苦得來的學術成果受到社會廣泛質疑,他們必不高興。所以一見學術腐敗浮現,正直的學者都要與其劃清界線。嚴厲懲處,正是提高學術腐敗的機會成本的方法。
基於上述原因,西方一流學府對學者的要求極高。他們要想獲得終身教職,便必要過五關斬六將,文章要在權威刊物出版,接受審稿人大量吹毛求疵、甚至無理的質疑。經過這種洗禮,他們對學術純潔性的執往往十分強烈,抄襲偽造等行為,死也不肯做。
香港學術界可為內地借鑑
但是,中國的學術腐敗為何如此普遍?學術是非的觀念在一部分人中又如此薄弱?除了學界的晉升體制不發達、被發現「造假」後又無懲罰外,其激勵機制亦大有問題。內地大學往往用獎金或房屋等方法鼓勵學者投稿。
清華一位朋友告訴我,他們若能在《自然》或《科學》出一篇文章,可有五十萬元獎金。小兒今年有一篇論文在《自然》刊登,他聽到內地五十萬獎金後羨慕不已,這已是他當學生幾年的收入了。上述武漢大學的研究也有發現,在內地偽造論文的生意,在去年市值約十億元。
造些假資料,包裝成一篇驚世巨著,有望可得大額獎金,總會有人肯鋌而走險。但如此一來,國際上的權威刊物卻要常常把內地學術腐敗拿來當話題,加以防範,中國學術界又情何以堪?
科技水平對一國的國力影響重大,而學術腐敗肯定拖慢科技發展。中國如何才能擺脫學術腐敗的羈絆?《自然》的編輯們認為,法律懲處作用不大,因為法律界中人根本不懂學術問題。互聯網使「造假」容易暴露出來,但網民科學知識不足,常會在不同陣營互相指責,做不到毋枉毋縱,最好的解決方法,還是倚靠學術界本身建立機制。
在這方面,香港倒可以做到重大貢獻,香港學界遠為潔淨,而且對建立現代學術規範經驗豐富,我未聽過外國期刊會對來自香港的論文抱有特別戒心。
香港學者與內地學者交流頻密,回內地幫助建立實驗室的人如過江之鯽。香港學術界的規範,在中港兩地學術界的長期來往中,應可起到很大的積極作用。
-------------------------------------------------------------------------
雷鼎鳴
學術腐敗與貪污腐敗
上周二張五常在本報發表大作《腐敗不是學術失敗的原因》,內中有不少篇幅論及我七月十九日刊出的《中國應嚴厲打擊學術腐敗》。記憶所及,五常老兄性喜作離群之馬,極少評論別人在報刊的文章,此次破例出手,使人驚喜。但究其原因,自然是因為他對中國的學術發展思茲念茲,無法放下不顧所致。
張五常文章中觸及拙作的主要部分,似乎是認為我相信,沒有學術腐敗,中國的學術研究便可搞上去。我沒有這種「本末倒置」的觀點。就算中國的學者全部都童叟無欺,當然不等於學術風氣便可大盛。我認為學術腐敗與學術沉淪有一種辯證的因果互動關係。一個地方的學術氣氛若果濃厚,抄襲造假受到鄙視,機會成本增加,腐敗行為的確會減少。例轉過來,若學術腐敗成風,大家忙於欺騙,學術發展卻不可能不受掣肘。
學術腐敗不但是漠視知識產權及欺詐的失德行為,對社會的經濟發展亦十分不利,但卻是極難根治的問題。科技學術水平高如麻省理工,十多年前便爆出過生物學家諾獎得主巴迪摩爾(David Baltimore,當過洛克菲勒大學及加州理工的校長)的實驗室,有一名博士後僱員造假,其後麻省理工調查得當,巴迪摩爾本人終於洗清嫌疑。
學生作弊非絕無僅有
有在大學教過書的人都知道,學生作弊絕非絕無僅有。據說,普林斯頓採用榮譽制,學生考試不用找人監考,而學生自動不會作弊。但此乃是學林異數,其他名校也不敢仿效,更遑論入學標準遠低的州立大學。
是否多作道德教育便能杜絕學術腐敗?這是天曉得之事。中國人發明了考試制度,考科舉的學子無不要飽讀聖賢書,但他們沒有人作弊嗎?多年前,我在芝加哥的自然歷史博物館參觀,見過一塊一兩方呎的絲絹,密密麻麻的用娟秀字體把《孟子》全部抄下。
據博物館解說,此布原本暗縫於某科舉考生衣服之內,以便其「出貓」。當年,我正修讀宋史專家先師克拉奇(Edward Kracke, Jr.)的中國科舉制度課,克師有天上課時突然拿出他珍藏多年的一塊古董「貓布」(不記得是宋代還是明代的),我告訴他自然歷史博物館也有,他聽後連忙追問,失望之情溢於言表,以為是罕有的收藏在海外也可容易找到,市場價值大跌也!學術腐敗,古已有之。利之所在,聖人倫理教化之言似無效力。
學術造假及打假的博弈是千古之爭,今天仍然繼續,但技術水平卻與時並進。以前學生考試作弊,主要通過在易於隱藏的小字條或手掌上寫上提示,或目必斜視「觀摩」別人的答案,科技含量不高。但今天電子儀器體積細小功能宏大,上課的筆記或課本,可輕易藏於「計算機」或電話之中,監考人員往往疲於奔命,考試中途學生上廁所也不能不伴隨左右。
考試以外,論文作業亦可輕易在國際市場購買。不同的老師自有不同方法對付,其中近來開始流行的一招,便是購入軟件,通過言文對照,看看交來的「論文」是否抄襲所得。此種軟件,據說已為美國的「教育測驗所」(ETS)所用,監察尤其來自東亞考生在GRE等國際大試中有無抄襲。
補習社成學術造假溫床
廣義地看,香港的教育制度及以提供「貼士」為本業的「補習社」實是助長學術造假的溫床。考試中若有考題要學生分析某某事件,不少學生若一早便有「貼士」,其實也只是在死記背誦別人提供的「標準」答案,並非自己的見地。這也是抄襲的一種,一代一代人的創意便是這樣被消磨掉。
最嚴重的學術腐敗,應該是偽造實驗結果或數據。此事誤導他人走冤枉路,害人不淺。但此種造假,其實需要高度的專業知識及才智。作弊者起碼要懂得怎樣使到自己用虛假證據所構建的結論被人重視,否則學術期刊不會刊登。他們若然知道腐敗之路走不通,改把精力放在真正學術之上,成就或會不錯。學術腐敗最大的社會代價,可能便是才智及精力的誤用及浪費。
學術腐敗與貪污腐敗有什麼異同之處?二者的定義及範圍便頗有不同。學術腐敗一般泛指抄襲剽竊別人的知識成果,或在學術問題上造假行騙。貪污腐敗是指有人以權謀私。更精準的定義是,社會或組織委託某人(例如官員)按既定的規則配置資源,但此人卻利用給予他的權力,違反了規則,使到自己或他所偏幫的人得到利益。
貪污腐敗可成「潤滑劑」
我想不出學術腐敗能為社會帶來什麼好處,但貪污腐敗很多時卻的確可成「潤滑劑」,使資源配置效率更高。中國改革開放以前,房價及租金被嚴重壓抑,表面上住屋便宜,但建屋卻是必然賠本,所以房屋供應嚴重短缺,很多情況等待十多年,也因無法分配到住房而結不了婚,苦不堪言。
當年我到廣州遊歷,喜歡晚間到海珠橋附近岸邊觀看市民生活。在極度昏暗的路燈下,可見一張一張長,每張都被兩對情侶共用,大家背對燈光,旁人看不清樣貌,便可作種種只適宜室內的活動。
面對此種困境,最想得到住房的人很可能要走後門,賄賂官員早日分配到房子。他們付出賄款,其實是等於用更高的價格取得房子,這樣做是部分、但不完美地恢復價格機制的配置功能。讀經濟的人都會知道,通過價格機制配置資源,在一般條件下,可達巴列圖效率(Pareto efficient),這比起官員把資源隨機胡亂配置,效果好得多。
不過,貪污腐敗與學術腐敗一樣,長遠的影響力也是十分負面的。貪污腐敗必涉及濫權,但權力對絕大部分人而言,卻絕非唾手可得。要獲得權力要先學懂怎樣「上位」,而所用方法通常與奉承賄賂有關,把精力才智用在此道,對社會生產無甚貢獻,是社會的巨大浪費。當掌權人通過過去的投資而得到權力後,他們必會捍著自己的權力基礎。
正如學術腐敗一樣,貪污腐敗也會造成浪費及不公,必須遏止。治標不如治本,什麼事最能動搖貪污腐敗的基礎?
有人認為是完善的法制。加強執法及懲罰,的確可產生一些效果,香港的廉署便是成功例子。但嚴格來說,這也只是治標之法,執法時偶有疏忽,利之所在,貪污腐化恐怕也會春風吹又生,貪官又會熙來攘往,無處不在。
道德教化如何?對投下巨大資源取得權力的貪官而言,這恐怕是陳義過高,對牛彈琴。更不可靠的是,道德標準往往會隨制度而起變化。舉個例子,現代工業社會不喜歡裙帶關係,靠關係走後門不會被認為是道德高尚之事,這種習慣與工業社會的發展格格不入也。
但自農業社會脫胎出來的內地社會,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仍被不少人認為是理所當然,符合倫理之事。如果有正直的掌權人拒絕理會鄉里親朋所走的後門,不一定會得到稱讚,有時反而會被定性為不念親情、冷血無情,罵他的人可能還自覺義正辭嚴。
助長權貴資本主義
最能動搖貪污腐敗基礎的是競爭的自由市場機制。二十年前,在內地買一輛名廠鳳凰牌自行車要五百多元,但卻要走後門。今天,一輛不錯的自行車二百元左右便隨便買到。要不要走後門付賄款?絕對不需要。若有人提此要求,跑到另一與他競爭的商店購買便可。在完全的自由市場機制下,不是貪官不貪,是沒有人肯賄賂他們。市場機制削弱了官員的壟斷權力,從而也使貪污失去基礎。阿頓勳爵(Lord Acton)的「權力導致腐敗」論,今天仍是至理明言。
中國經濟改革開放過去的成功,與資源配置逐步市場化及相互競爭的民營企業湧現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見去年秋天我在本報刊出的關於中國建國六十年的系列文章)。國企佔用社會大部分資源,但產量卻長期不及民企。
中國政府一直容許國企的存在,但今天國企與民企的利益衝突漸漸變得尖銳,阻礙著改革,也拖慢經濟增長。一些要捍衛著舊有制度的所謂新「左派」卻大力鼓吹政府應多干預市場。
內地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對「國進民退」深以為憂。市場干預製造了新的權力,會助長「權貴資本主義」,腐敗行為只會更為普遍。吳敬璉的觀點,與我二十多年來對貪污腐敗研究的結論頗為接近。
2010年8月9日星期一
腐敗不是學術失敗的原因
訂閱:
發佈留言 (At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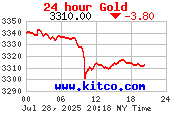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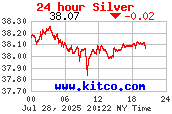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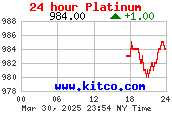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