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五常
不少讀者期望我寫這篇文章,應該寫。不易寫,但應該寫。中國是個古國,其歷史複雜無比,文化的演進沒有歐洲十五世紀之後的閃閃生光,但純而厚,是好於學問的人的一個好去處,我是著了迷的。歷史說,解放立國到今天是六十周年了。北京要大事慶祝,顯然因爲六十年是一個甲子。中國的文化傳統有十個天干,十二個地支,能拼出六十個不同的組合,六十年是一個迴圈。爲何有這樣組合的安排我可沒有考究,但中國的傳統是以六十爲大壽。不管你同不同意,或是否反對一個國家久不久應該發一下神經,你不能不承認中國要做大事可以做得非常大。去年的北京奧運是一例,明年上海的世界博覽會是一例,今天是二○○九年十月一日,打開電視看看吧。
建國六十年,剛好有三十、三十之分。前三十解放共用,不妥不妥;後三十開放改革,很好很好。後者,我在《中國的經濟制度》的結語中,有所感慨而揮筆直下:
「這些年北京做出來的大可引以爲傲。你可以詳盡地批評執掌政權的人,但他們減少了那麽多的貧困,工程之龐大與迅速,歷史從來沒有出現過。我認爲這樣的成就不會再重復——不管是何地,不管是何時。」
我是個生存在上述的整個甲子的人。六十年前的十月一日,我快十四歲,懂事的。不斷地跟進中國的發展,對歷史有研究。在美國讀本科第二年時,我寫了一篇關於鴉片戰爭的前前後後的長文,當時的經濟歷史教授Warren Scoville給予高評價。今天我想,如果沒有上文提到的不妥的前三十年,中國會有很好的後三十年嗎?如果六十年前解放之初就動工三十年後的改革,中國今天會更有成就嗎?前三十的不妥是要付代價的,這代價高,值得嗎?這些問題我沒有答案。我只能說,從歷史規劃下來的局限看,中國能達到今天的成就,是人類歷史沒有出現過的艱巨工程帶來的奇迹。這樣的成就當然要付代價,很大的代價,至於這代價是否值得,見仁見智,是主觀的判斷了。比較客觀地問,如果中國選走另一條路,這大代價會否低一點?今天的人恐怕沒有答案;將來的歷史學者總要提出這個問題。
讓我從乾隆皇帝說起吧。此公是二百五十年前的人。記不起正確年份,當時英國的皇帝派一個欽差大臣訪中國,要求發展貿易。乾隆接待了他,寫了一封歷史有名的信給他帶回英國皇帝。該信的大意是說:「我們中國什麽都有,對西洋鬼子的産品毫無興趣,而作爲中國皇帝,我的責任是搞好中國的民生,番邦要求的外交事宜,與我何干哉?」這是當時中國閉關自守的意識,百多年後,八國聯軍的年代還是差不多,但八國聯軍之際,中國已經遠遠地落後於西方了。
我們當然不懷疑古時的絲綢之路打通了一點與歐洲的聯繫,也不懷疑明初的鄭和下西洋是比哥倫布早上大半個世紀的偉大探索。然而,無論怎樣看,中國曾經有數千年的閉關自守的日子。康熙謝世前三年(一七二○)在廣州設立公行,容許行商與老外貿易,只是爲了應酬一下,說不上有發展外貿的意圖。康熙是個好皇帝,但他對西方科學的興趣只是爲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圓明園的故事與後來的悲劇是清代皇帝的好奇心奢侈化的結果。中國打開門戶是鬼子佬用槍炮攻開的。鴉片戰爭之前,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檔案與英國商人催促政府出兵的文件,我讀過。他們要中國的絲茶,但中國只要他們的銀兩,銀兩不夠,他們在印度找到中國人愛吸的鴉片。
一個聰明的民族,關起門來發展自己的文化,大有可觀,但與西方的文化傳統很不相同。中國的文化既深且厚,可惜到今天西方的衆君子對中國文化的理解與體會,稱得上是及格的寥寥無幾。中國的學子沒有幾個不知道有莎士比亞這個人,但西方的學子沒有幾個聽過蘇東坡。今天,在鋼琴上彈莫札特彈得像樣的中國孩子數以十萬計,但我賭你找不到幾個西方的孩子懂得唱京曲。是一面倒的西方影響中國,只是近幾年西方的孩子們搶著學起中文來了。後者是大好形勢,反映著西方的衆君子終於察覺到地球上還有另一個重要文化存在,是值得尊重的。這是我對國家六十有感中的一個很好的感受。
一面倒的中學西,有貶意說是崇洋媚外,但其實是清末民初以還,早一點說是乾隆皇帝之後,西方的科學與工業産出比中國的先進得太多,把炎黃子孫嚇破了膽。讀得出幾個英文字的誇誇其談,把西方的一切捧到天上去。一九五七年我離港赴北美時,護照是五千四百多號,即是說從盤古初開到一九五七,從香港正規外出的只有五千多個。急起直追,進入洛杉磯加大的第二年被邀請作西方藝術史的助理教員。好奇地跑到圖書館去研讀一下中國的藝術文化,客觀地衡量,知道那所謂落後的中國,其文化了不起,自成一家,影響了梵高、高庚、畢卡索等西方天才大師,可惜深入的影響卻說不上。我對中西雙方的文化一視同仁地重視,是從那時開始的。東歸東,西歸西,二者混合不來,是老生常談,但不對。
今天看,中國走現代化的路是成功了的。雖然還有好一段要走,但回頭看,我們的確走過了千山萬水。乾隆之後炎黃子孫的經歷滿是血淚。抄襲西方不容易抄得有好效果。西方有的不是一般皆可取。近幾年凡是抄襲西方的經濟政策,差不多一律不妥。說真的,今天中國的經濟改革有成,主要是靠中國人自己想出來的方法。
千山萬水,炎黃子孫今天大可披襟岸幘。重要的問題,是中國人既然那麽聰明,那麽吃得苦、有幹勁,爲什麽要花上兩百年的時間才走出那漫長的黑洞呢?我找到的答案,是在閉關自守的日子裏,中國的傳統是以風俗倫理管治,高舉儒家學說,重視三從四德。學而優則仕,蘇東坡等天才都做官去了,其中不少以倫理判案。沒有司法制度,傳統上中國沒有律師這門專業。也因爲讀書的人材都求做官,中國沒有出現過一個阿基米德(西元前二八七至二一二),或一個伽利略(一五六四至一六四二),或一個牛頓(一六四二至一七二七)。不是智商有所不及,但學而優則仕,好學的讀古書,談詩詞,習書畫,騰不出一個科學發展的空間。
不要貶低以道德倫理治國,不要嘲笑三從四德。從一個以農業及手工藝爲主的經濟社會看,這種管治制度可取。無可置疑,中國的傳統農業與手工藝了不起。就是到了上世紀四十年代,美國大名鼎鼎的農業經濟專家卜賽(賽珍珠的丈夫)跑到燕京大學研究中國的農業幾年,拍案叫絕,認爲比西方的高明得多了。
我說不要貶低以道德倫理治國,因爲這種治法成本低,遠低於司法制度。從一個不論科學、不靠科技産出的社會看,以一個靠家庭的農作與手工藝而爲生計的社會而言,高成本的司法制度不可取。然而,以道德倫理治國的一個大麻煩,最頭痛的,是沒有彈性,修改不易。今天我們知道,法律是可以修改的,但道德倫理修改極難,事生於世而備適於事,經濟的需要轉變了,但管治的制度改不了,可以帶來災難。四十年前在芝加哥我與戴維德(Aaron Director)研討過,得到的結論,是管治成本愈低的制度,愈是沒有修改的彈性。我們當時比較的是英國的普通法與歐洲的大陸法,認爲普通法的施行成本較高,但比大陸法容易修改。再相比,要放棄道德倫理的準則而以司法制度代之,更是難上加難。
三從四德的家庭傳統,跟道德治國合得來,在重視農業、手工藝甚至商業而言,這樣的管治制度因爲成本低,可取。困難的出現,是人口上升,不靠工業的發展不足以糊口。歐洲在十八世紀初期的經濟學有重農主義,也有重商主義,但沒有重工主義。然而,一七七六史密斯發表他的《國富論》,以專業分工合作的制針工廠起筆,明顯地是重視工業發展的思維。說來湊巧,一七七六是乾隆皇帝的時代。想當時,中國以家庭爲産出單位,但歐洲的工廠運作已經發展得如火如荼了。
工業的發展要讓家庭産出轉到工廠去,歐洲早就跑過了這一程。中國呢?要到清末民初才見到工廠形式的出現。這發展需要年輕人離鄉別井,跑進沒有親屬同事的工廠操作。這樣,以家庭産出的傳統開始瓦解,成本較低的倫理管治逼著要轉到司法或法治那方面去。談何容易,就是今天,好些中國的家族傳統的意識還在神州存在。我是個保守的人,不認爲中國的家族觀念或禮教沒有可取之處。是的,我不認爲西方的子女要向父母借錢求學是好品味的風俗。但我希望讀者明白,從以家族爲基礎的道德倫理的管治制度,轉到近于六親不認的管治制度,是多麽困難的一回事。
像香港那樣的一個小地方,或像日本那樣的一個小國,上述的轉變遠爲容易,或衝擊比較小,但中國地大人多,民族這裏不同那裏,口音不一,就是連吃,地區之間也大異其趣,需要的轉變難於登天。二戰期間,我在廣西某農村住了一年,知道村與村之間不論婚嫁,口音不同,更談不上搞什麽合作産出了。那只不過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今天呢?深圳人口一千三百多萬,其中一千三百萬是外來的。
上文提及,國家六十年,前三十不妥,炎黃子孫付出了大代價。代價不論,我的直覺是沒有這前三十中國不會有今天。代價是成本,但經濟原則說,歷史成本不是成本,我們要多向前看,不要頻頻爲以往的代價惋惜。另一方面,單看今天北京要慶祝的六十年,我們會低估了中國人的成就,或誇張了昔日的代價。爲寫此文,我決定向歷史多走幾步,細說從前,用上的解釋是自己的以社會費用的轉變爲基礎的制度理論。這理論是三十年前我爲推斷中國會走的路而想出來,今天是多了三十年的觀察而改進了。
不堪回首的日子二百年,大可回首的是中國數千年的文化,其中好些值得探討,值得欣賞。中國的青年呢?昔日的代價他們沒有付出,但新的機會就在眼前。他們要學我當年,見到有爭取知識的機會就站起來大博一手。爭取將來當然是今天中國青年應走的路,而在走這路的同時,他們也要學我當年,不斷地探討中國的舊文化,與西方的比較一下,從而體會到學問這回事是沒有中、西之分的。一面倒的中學西曾經是悲劇,但上蒼有眼,昔日的悲劇今天變爲喜劇了。是的,在地球一體化的今天,中國的孩子們占了先機,因爲中西兼通,將來的天下他們會是主角。這也是我對國家六十有感中的一個很好的感受。
孔子雲:「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三十年前的開放改革,無疑是「立」。今天六十,「耳順」要怎樣解才對呢?鄭康成雲:「耳順,聞其言,知其微旨也。」皇《疏》雲:「聞其言,即解微旨,是所聞不逆於耳,故曰耳順也。」翻過來,我的解釋,是耳順指懂得分辨是非,知所適從,可以作出大智大慧的判斷。謹以此爲北京的朋友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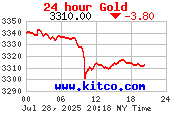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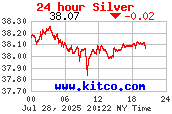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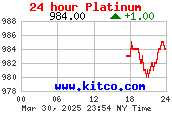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